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517篇原创首发文章
“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军登陆点作战,在平原和街巷作战,在山野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如果1940年5月那场撤军行动以英法联军的失利告终,恐怕邱吉尔在下议院的满腹慷慨之词就无法流传。虽说“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不应被蒙上胜利色彩,但并非所有的失败都毫无价值。
战争中最重要的是人,如果敦刻尔克被围英军悉数遭俘,这个实行志愿兵役制的国家就会霎时瘫痪陆上抵抗力量。“当40万人无法回家,家为你而来”,9天9夜、34万联军被救援,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新片《敦刻尔克》表现的正是这段撤退奇迹。这部惊世之作规避了宏大叙事与抽象思考,镜头对准的是个人在战地逃亡时的真实状态,极度克制和有限的信息中坦露的不是回忆与备忘,而是正在发生的抵达,一切因此充满悬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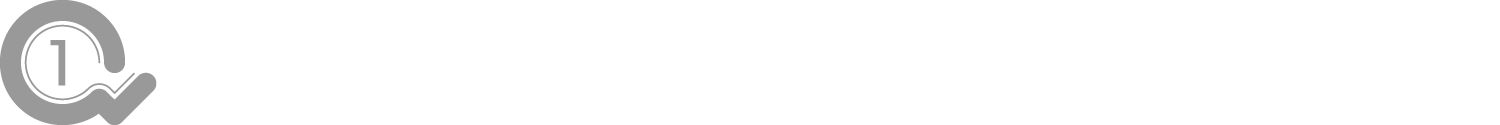
反传统的《敦刻尔克》
真正优秀的创作者永远富于创新精神、永远领先于时代,永远能够在颠覆传统的同时引领审美哲学,被誉为艺术情怀与工匠追求完美结合的诺兰便是此中翘楚。作为在大预算和创作自由的平衡间随脚出入的“神导”,他的这部《敦刻尔克》与传统战争类型片相较虽显得感官十足,但缺少的部分似乎更多:没有常规意义上的战争场面、没有女性角色、没有大段对白和复杂戏剧冲突、甚至连敌人的脸都没出现一张。不煽、不燃、不虐、不苏、不热闹的《敦刻尔克》,基本具备了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票房扑街的一切特征。但这部反传统的《敦刻尔克》却是最好的战争片,它摒弃了脸谱式大人物的历史在场,而以库布里克式的冷静、精简和希区柯克式的悬念、奇想重构了敦刻尔克海滩上个体逃生的细节与温度。
电影发展到今天,再大的战争场面在投入足够的前提下已经不存在无法实现的可能,而诺兰偏偏又对高概念电影(高关注度、高传播性话题)的处理驾轻就熟,因此他选用求生本能而非英雄主义来还原历史乃有意为之。在这份将“撤军大业”拍成悬疑惊悚片的决心背后,《敦刻尔克》潜移默化间也完成了对“诺兰风格”(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新黑色电影风格、有限信息中的复杂情节)的部分舍弃。罕有战争主题会用撤退这个角度,更罕有叙事电影会以降低故事性、抛弃情节弧线的手段展现战争的残酷。当诺兰粉已经习惯了《盗梦空间》和《星际穿越》的烧脑,诺兰这次使了招删繁就简;当观众已经捂好耳朵准备感受震耳欲聋,《敦刻尔克》却复刻了坠针的声音。在这部创作者自言的“逃生电影”中,习惯于误导和操纵观众的期待从而实现超群效果的诺兰以一种反传统又反诺兰的方式再次实现了对观众预想的跳脱和反制。

《敦刻尔克》最复杂的一点正在于无论是对于战争电影还是对于诺兰电影而言,它都突然变“简单”了。这种简单的背后是诺兰惯性思考的复杂,这是一次面对传统叙事逻辑的战略撤退。诺兰相信电影永远不能创造完整的世界,那些空间和缝隙应当被合理利用:没有展示出的部分会成为一种优势,实现对已创造的有限世界的解放。而这次被诺兰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的除了这桩历史事件的核心——时间,还有在被压缩的时间里个体在战争面前的渺小和对未知的恐惧。《敦刻尔克》之所以拒绝过度戏剧化正因为比起剧作真实和历史背景真实,诺兰更相信历史现场某个时刻属于经历者的感官真实——“关于他们遇到的人,关于身体,关于他们所面对的物理现象:水、海滩的声音、找到一个活着去海边的方式。”
《敦刻尔克》的冷峻与凝练恰好与战地本身的压抑与紧张高度贴合,在面目模糊的人物与指向不明的台词的集合中,是关于生存以及逃亡情景的犯罪式复刻。那些必要空隙的存在不仅提醒了事件的全貌,更丰富了电影对于冰山一角的勾勒和阐释,诺兰在创作手法上的反向操作与以守代攻,完成了对历史还原的从无到有和后发先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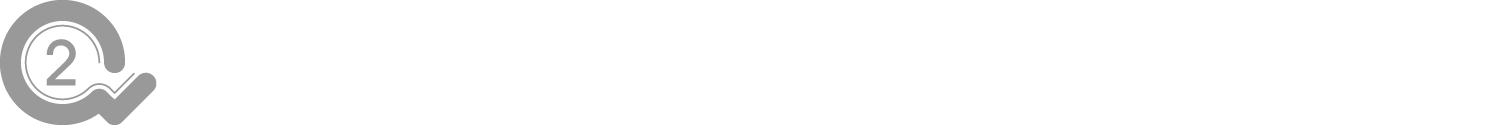
撤退的细节
在《敦刻尔克》中,诺兰用不同角度并行的三条线来讲述陆地、海面和空中发生的故事:陆军海滩求生(对应时间为一周)、平民海上救援(对应时间为一天)、空军阻击敌机(对应时间为一小时),“陆海空”的交叉剪辑堪称错落有致、天衣无缝。值得注意的是,包含在诺兰非线性叙事套路中的编导意识探索的是个体内心深处的精神信念。

《敦刻尔克》镜头聚焦的全是小人物,没有狗血、没有卖弄聪明、没有往死里打,只有“个人史诗”般绝地求生的精神风骨,只有被无数个体命运所冲淡的个体在时代暗夜里的归心似箭,“即便是在观看者的心中,他们也不被期待成为英雄”。虽然这场大撤退从不为表现刻板的英雄主义,但这不并代表它的细节里没有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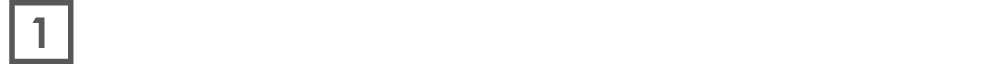
细节一:守军的抵抗
电影开场是充斥着冷枪和恫吓传单的封闭街巷,巷道内惊惶的英军士兵正是被困联军的缩影。年轻的士兵汤米躲避枪弹翻过栅栏,枪声尾随而至,直到他越进法国盟友的战壕才稍获喘息之机。一个法国兵对他喊:“一直往前跑,不要回头”,汤米一路狂奔直至敦刻尔克海滩,而他的身后则是留守掩体向敌军还击的法国盟军。
历史上为保证撤退的顺利进行,驻守外围的联军付出了重大牺牲:加来海峡的一个英军步兵旅和坦克营被严令禁止撤退,他们牵制了德军装甲师4天之久;里尔的法军第一集团军在司令布尔夏尔的带领下英勇抵抗、拒绝后撤;敦刻尔克西部与西南部驻守的法军第十六军团共4万余人为断后全部被俘。虽然电影留给后卫部队的镜头很少,但正是他们的坚持战斗才换来了大部队的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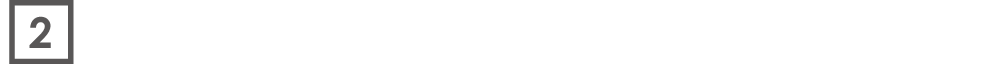
细节二:逃生中的义举
海滩上的主旋律是逃离,电影先是表现了死亡重压下人性真实的一幕:汤米与沉默的法国士兵吉布森搭成逃亡二人组,他们出于利己考虑救起被遗弃的伤兵,一路抬着担架、在成千上万排队等待的士兵无可奈何的眼神中率先上了军舰。当我们还来不及用道德来衡量他们的私心,汤米和吉布森却分别完成了对“污名”的洗白:当军舰被鱼雷击沉,是吉布森游到闭合的舱门口,全力拧开舱门,帮助挣扎者逃生;当有沉船风险的商船需要有人弃船,英国士兵诬陷法国人吉布森是纤细、让他当替死鬼,汤米站出来阻止同胞对友军的胁迫,他用良知顶住了人性恶的枪口。或许诺兰想让观众思考的是:汤米和吉布森都是普通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利己的求生欲望,但我们是否和他们一样具备那份危难时的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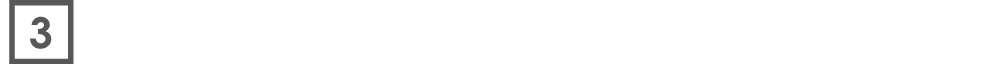
细节三:“月光石号”的勇气
真实二战史上,撤退伊始英法比荷政府便征集民船以供救援。英国民众听说自己的军队受困,自发驾着游艇、拖船、救生艇、蒸汽船、渔船跨越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赶赴炼狱般的敦刻尔克海滩。这些平民以牺牲125人的代价救回大约10万名士兵,电影中的“月光石号”便是民船的代表,围绕在船长道森、其子彼得、帮工乔治等人的这条海上叙事也成为《敦刻尔克》中唯一留下金句的段落。当道森船长救起的那个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士兵出于恐惧阻止“月光石号”驶向敦刻尔克时,他冲着老船长说:“您这么大年纪就该在家呆着,管这事干啥?”道森回复道:“我这个年纪的人发动战争,不能总让年轻人去送死。”

至于阻止这位军士抢夺船舵时不幸重伤身亡的17岁少年乔治,虽然他连想救的大部分人的面都没见着、虽然他是被本该保护他的士兵失手打死的,但他却是敦刻尔克的英雄。英雄的含义不在战斗力,而在于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和义无反顾。当道森船长说他们是去战场接人,跳上船的乔治坚定地回应:“我能帮得上忙。”这位智力和见识或许都很平庸的男孩,在危急的关头却心怀勇气与信念,其善良和奉献令人折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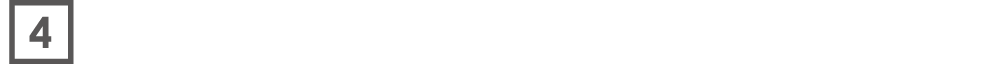
细节四:空军的隐秘战斗
空战戏是影片高潮,虽然它只占用了九天剧情中的一个小时。这条符合国内观众审美的“空线”中有接战场景,同时也是三条线中紧迫感最强的一条:要在一小时内执行掩护任务,还需计算油耗,搞不好还得来个高难度海上迫降。《敦刻尔克》的写实体现在细节上,空战英豪可不是“天高任我飞”,而是油耗表坏了都得时刻问同伴拿笔记着、同伴被打落了只能自己算着、在保守返航与阻击敌机(燃料殆尽被俘)之间进行取舍。
历史上的英国空军为掩护撤退计划、每天出动300架次到敦刻尔克上空同敌机交战,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是滞留在海滩上的陆军只能感受到自己饱受轰炸,很难看到本国飞机在几英里以外或者云层上与敌机殊死搏斗,故一度对空军持有愤怒情绪——“当陆军在多佛尔或泰晤士河港口登岸时,还侮辱了穿着空军制服的人”。电影中也反映了撤退者与掩护者由于信息不对等而产生的误会,当“月光石号”靠岸后,打掉了德国飞机、自己也九死一生的飞行员柯林斯被陆军质问道“你们空军干嘛去了?”不过受了委屈的柯林斯还是得到了道森船长的安慰:“船上的人都知道你们的付出。”电影结束前的桥段,飞行员法瑞尔驾驶着那架燃油耗尽的喷火式战斗机当着海滩上陆军的面打下了德军战机,这是诺兰对于历史的一种致敬,他希望英雄在当时就能接受到万众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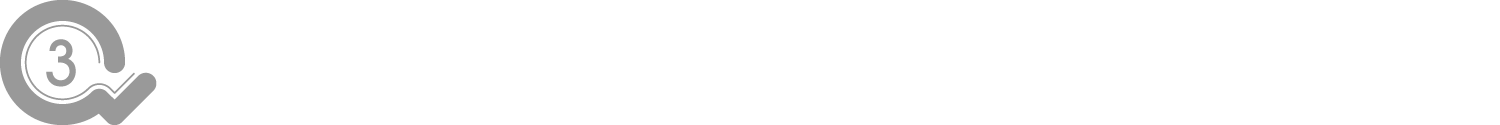
以退为进的重量
诺兰曾经在采访中提到:“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会不断去寻找文化中的罅隙和缺口,不断发掘那些未曾被讲述过的伟大故事。”《敦刻尔克》正是这样一个伟大故事,它以战争为载体,其内核仍是人性。诺兰把这份人性搬上银幕的初衷始于1995年,他曾驾着帆船历经19个小时从英国抵达敦刻尔克,一路想象着在炮火中渡海的二战士兵。诺兰这点和拍过《赛德克巴莱》的台湾导演魏德圣很相似,后者少年时代就了解到雾社起义,直到他拍成名导后才对心存多年的宏大题材破土动工。在诺兰积累经验和砥砺技巧的20余年中,他常将动作特效和关于现实概念的棘手问题结合起来从而带动观众对人性和人的主观意识进行深入思考。
轮到如何呈现这场撤退以及撤退后面的内容,诺兰的《敦刻尔克》确立了以退为进的指导方针——退出了宏观概述,进入了微观叙事;退出了正典备忘,进入了田野调查;退出了标签化的类型之作、进入了原生态的个体经验。诺兰相信,当观众普遍对依赖场面、渲染情绪、发扬精神的战争片套路审美疲劳后,唯有在微观层面的独辟蹊径才能引起讨论和思考。被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的诺兰试图在历史真实与观众体验间寻求一种平衡,他希望严肃对待这个主题、希望观众真正关心角色的命运,所以“掐头去尾”的《敦刻尔克》不交代历史背景和伤亡人数,而是结合普通人的遭遇处处体现了一种内在的紧张。人们在对战争题材的浅薄化处理中浸染太久,便会遗忘战争的本质是场灾难,而《敦刻尔克》的意义便是通过微观渠道找到了一条今人与历史联系的纽带。

影片引起的讨论正如那句话所言——“看《敦刻尔克》所需的情商,高于看《盗梦空间》所需的智商。”电影中有个桥段,救援行动一筹莫展之际,海军将领看到了冒死前来的平民船队。
左右:您看到了什么?
将军:我看到了祖国。
电影原声中的“home”在这里到底应该翻译成“家”还是“祖国”?如果这里的“home”是祖国,为何前面的那句“你该回家养老”没有翻译成“你该回祖国养老”?这是一种声音。但笔者倒认为“顾信则不达”,这里对“home”的翻译正如编剧史航解释的那样——“当士兵撤回不列颠本土,沿途民众只说谢谢你回来。什么是祖国,祖国由你那些通情达理的同胞组成。” 就像道森船长的那句 “敌人打过来,哪里还有家” ,要知道对岸的士兵未必都是平民的家人,如果真的把“home”翻译成家,何以解释救援者的蜂拥而至?《敦刻尔克》的逻辑是“家能够代表国,国可以保全家”,它没有陷入“有国才有家”的单一逻辑,更与那种“某个士兵拿出护照,上书烫金大字:英格兰永远在你身后”的乌托邦式处理大相径庭。
电影中“家与国”的微观辨证让笔者想起日本史料记载的一桩真实事件:徐州会战的某次战役,日军以压倒性优势攻克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守军除了一名炊事员受伤被俘、从指挥官到马夫全部战死。日军清理战场时发现了国军机枪手的手腕和机枪之间绑着一副镣铐,于是招来随军记者准备对此大做文章。侵略者询问俘虏这些战死的守军是否是被抓壮丁强迫来打仗时,得到了令他们震撼的回答:这名机枪手的家就在阵地后面的村庄,镣铐是他自己锁上的,钥匙当场扔到了河里。 他的慷慨赴死,是卫国,也是为家。

有人说《敦刻尔克》拍的是和本国无关的历史,令人兴致索然,这不过是借口。因为诺兰的剧本里是非常普世性的故事,它讨论的是“一副担架的地方可以站7个人”这种事关伦理的换算方式;是明知战场如炼狱般残酷,仍有人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是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在灾难中的无私和高贵。它的确存在与爱国主义重合的部分,但它不会沦为煽动基本情绪的工具。它敦厚、理性、温和地体察了求生者在绝境中的信念,它绕过战争的熔炉给予死里逃生的生命应有的尊重与宽慰。它游荡在生死线附近,抹去了浅尝辄止的刻板纪念,于无声处留下人性的重量。
与国内某些军事评论者所称的“电影没有血肉横飞的展示、让他们看得不够过瘾”相比,法国主流媒体和学者对于《敦刻尔克》的批评则稍显“姿势水平”的正常——法国人坚持认为诺兰的电影淡化了法军的贡献。艺术毕竟不是历史,无须苛求它能面面俱到,法国人若希望讲述故事的正确版本,可以自己再拍。这个道理同样很普世,值得去联想——我们没有“敦刻尔克”,但我们有艰苦卓绝程度丝毫不亚于它的“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4000520066 欢迎批评指正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

